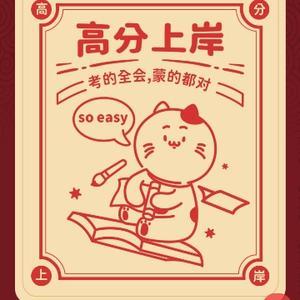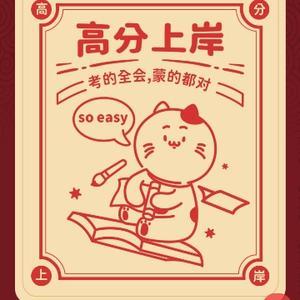
安逸
1957年,抚顺战犯管理所破例批了一间房,允许一对“夫妻”同宿一夜。这对夫妻,一位是末代皇帝溥仪,另一位,是被称为“最后的皇妃”的李玉琴。他们结婚14年,从未真正同过房。这一夜,终于同室,却也是诀别前的最后相见。一个身份尴尬的女人,一个废帝囚徒,这一夜,到底发生了什么?
房间里静得能听见外面雪粒子打在窗户上的声音,李玉琴把围巾摘下来,叠好放在板凳角上。溥仪坐着没动,眼睛盯着桌上那碗小米粥,粥都快凉透了,上面结了层薄薄的皮。李玉琴看不过去,伸手把碗往他面前推了推:“趁热喝吧,凉了伤胃。”
溥仪这才拿起勺子,小口抿着。他手背上有几道浅浅的疤,是前几天劈柴时不小心划的。李玉琴看见了,没说话,只是从布包里掏出个小铁盒,打开是些药膏,“这是我托人从长春带来的,治外伤挺好,你拿着。”
溥仪接过来,盒子有点沉,里面的药膏还带着余温。“你……现在日子还好?”他问得有点结巴,以前在宫里哪用得着这么小心翼翼说话,都是别人看他脸色。
“就那样呗,”李玉琴拿起自己的碗,喝了口粥,“图书馆的活儿不累,就是整理旧报纸费眼睛。前儿个还翻到1945年的报纸,上面有篇讲长春光复的,看着挺感慨。”她顿了顿,抬眼看溥仪,“那时候我还在宫里,以为日子就那样过下去了,哪想到现在能靠自己挣工资吃饭。”
溥仪放下勺子,手指在碗沿摩挲着。“我在这儿……也学了不少东西。”他声音低了点,“以前连鞋带都不会系,现在不光会种地,还能给所里的菜地搭架子。前阵子种的西红柿,结了好几个红的,管教说我种得比老农民还好。”说这话时,他嘴角好像动了动,像是想笑,又没笑出来。
李玉琴看着他,忽然觉得眼前这人跟宫里那个“皇上”一点都不一样了。那时候他穿着笔挺的制服,说话慢悠悠的,眼神里总带着股子说不出的距离感。现在他穿着灰棉袄,头发也白了几根,手粗糙得像老树皮,倒像是个普通的邻家大叔。
“其实我这次来,”李玉琴把碗放下,手在膝盖上擦了擦,“是想跟你说清楚。咱们……把手续办了吧。”
溥仪没惊讶,好像早就料到了。他点点头,从棉袄兜里掏出个皱巴巴的信封,“这是我攒的几块钱,你拿着。不多,算是……我给你的补偿。”
李玉琴没接,“钱我不要。你留着自己用吧,买点营养品。”她站起身,走到窗边,外面雪停了,月光照在雪地上,亮堂堂的。“我来之前就想好了,以后各过各的。你好好改造,出去了也能过正常人的日子。我呢,就在长春待着,守着图书馆那点活儿,挺好。”
溥仪也站起来,走到她身后半步远的地方,没再往前。“你说得对。”他声音很轻,“以前是我对不住你,把你圈在宫里,误了你这么多年。现在这样,对你好,对我也好。”
那天晚上,两人就分着睡在那张木板床上,中间隔着老大一块地方。谁都没说话,可谁都没睡着。李玉琴听着溥仪的呼吸声,想起刚进宫那会儿,他夜里偶尔会咳嗽,太监们忙前忙后地送药,动静大得很。现在他呼吸挺匀,就是翻身的时候床板“吱呀”响了一声,然后又安静了。
后半夜李玉琴迷迷糊糊睡着了,再醒过来天快亮了。她悄悄起来收拾东西时,看见溥仪已经坐在板凳上,盯着墙上的日历发呆。桌上的咸菜碟空了,两个碗也刷干净了,整整齐齐地摆在那儿。
“我走了。”李玉琴背起布包走到门口。
溥仪“嗯”了一声,从门后拿起她落在这儿的围巾递过去,“天冷,围上吧。”
李玉琴接过围巾,围在脖子上,暖烘烘的。她没回头,拉开门走了出去。外面的雪地上,管教员老王已经等着了,看见她就说:“早饭在灶上呢,吃了再走。”
李玉琴摆摆手,“不了,得赶早班车回长春。”她往前走了几步,忽然想起什么,回头看了一眼那间屋子窗户,窗帘拉着,看不见里面的人。她笑了笑,转身大步往前走了起来。雪地里的脚印一串接着一串,越走越远,再也没回头。
后来听说,溥仪收到离婚判决书那天,在所里的菜园里待了一下午,把那块西红柿地又翻了一遍。而李玉琴呢,回长春后第二天就去法院交了材料,然后照常去图书馆上班,同事问她脸色怎么这么好,她笑着说:“睡了个好觉,心里敞亮了。”
其实哪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,就是两个被过去困住的人,在一个普通的雪夜里,终于敢跟过去说再见了。他放下了皇帝的架子,她挣脱了“贵人”的枷锁,然后各自走进了属于自己的烟火人间。挺好的,真挺好的。